铜镜本是日常用品,但由于镜子能反光、能清晰映象,因而被人们引喻出许多社会功能,成为古人墓葬的随葬品。由于铜镜所具有的「破暗取明」、去魔压邪作用,再加上古代「视死如生」和「诸之具无不从者」的观念,人们把生活密切的铜镜同葬,以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
铜镜不但成为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当然,王公使用的往往是制作精良、纹饰精美的大尺寸铜镜,而一般的平民百姓使用的铜镜尺寸较小,纹饰属于普通常见的品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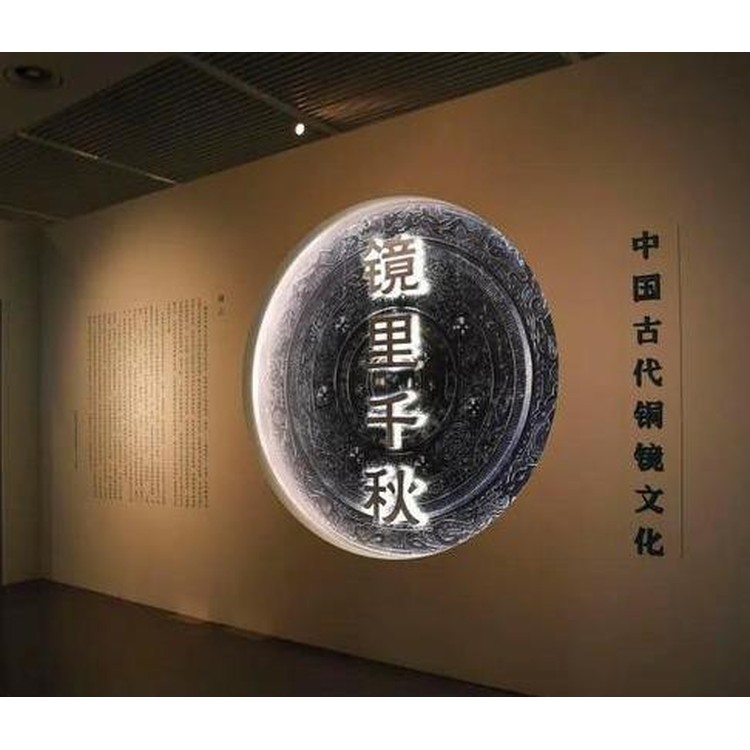
古书中提到的「山鸡舞镜」(《异苑》)、「化鹊捎信到夫前」(《神异经》)等故事,都与爱情有关,更成为许多诗文常爱运用的题材。这些美丽或凄然的故事,既表现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又说明了铜镜作为信物,其传承与纹饰内容是渊源有自的。考古发掘中也曾见到合葬墓中各持半面铜镜的实例。
镜子能驱邪照妖,是古代以至现代的传统观念,古人不理解铜镜映射的原理,以为铜镜可以发光,具有「法力」,可以照妖驱邪。很多道士修行、炼丹时都镜不离身;佛教和道教举行仪轨时,铜镜亦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器;有些人还以镜子作为镇宅的法器。这虽然未必符合科学精神,却也可以在精神和心理上,给虚怯的人以一点安慰。
由于镜背面积不大,纹饰所选用的题材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譬如祈求吉祥的心愿,表现为铜镜中常见的铭文如「常乐未央,奉毋相忘」;崇信神仙的思想,表现为仙人瑞兽的纹饰;道德的训喻,表现为借铜镜作鉴照真理的象征意义(如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或公堂上悬有「明镜高悬」的字样以示为官清廉);道教法象的运用,表现为借铜镜作法器;佛教艺术,则表现为以佛像故事作纹饰,如宋代的「达摩渡海纹镜」等等,这些内容无不反映出当时社会意识的特征,这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1959年,在日本福冈县饭冢市立岩堀田的瓮棺墓出土了一面汉镜,其铭文与西汉时期的铭文镜基本相同:「日有熹,月有富,乐毋事,常得,美人会,芋瑟侍,贾市程,万物平,老复丁,死复生,醉不知,酲旦星(醒)」。另外,1978年11月,在席巴尔甘(Sibrkand)贵霜早期三号墓中,也出土了铭文基本相同的汉代铜镜,这是汉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又一证据。
清末民初的学者罗振玉在《古镜图录》中形容铜镜:「古刻划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莫镜若也。」古铜镜随历史社会的发展而各有不同美态,形态、纹饰、铭文、内蕴、技艺等,各具特色,以下略取一二以作介绍。
蟠螭纹是一种变体的龙纹,形态多为盘曲纠结,穿插缠绕。此镜为三弦钮,云雷地纹。钮座外为宽凹面带环,内饰一人与三龙纹,人作奔跑状,龙作回首形,一龙脑后有角,有学者研究认为此纹饰是表现古代「刘累训龙」的故事(见《收藏家》2000年第8期《一面特的战国龙纹镜》孙克让)。且龙分公母,有角的龙为雄龙,无角龙为雌龙;主纹饰为三龙间以折叠菱格,三龙纹繁复夸张,龙口大张,露利齿,线条饱满富于弹性。素卷缘。此镜内区纹饰,目前尚未见于著录。

镜为弦纹钮,钮外一周宽凹面带,素地上面饰三兽纹,二猎犬,一兽,兽纹似虎似豹,猎犬的颈上有项圈,说明已是经人工驯养的猎犬,素卷缘。此镜的特点是没有地纹,三兽铸在光面素板上,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战国镜中出现浮雕兽纹的比较,其工艺制作难度大、要求高,再者,三兽孤伶伶地在素面板上也不够美观,而能够铸出此类浮雕兽纹的必定是工匠,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镜钮外的凹面带圆环的外缘与镜缘之间的镜面明显低凹,因此可以推断此镜的「素面」原来可能有填漆彩绘工艺,这样就使镜面与钮座及镜缘基本处于一个平面上。但是,经过二千多年的埋藏,当年的填漆彩绘工艺已经无可寻,尽管如此,此镜仍然是战国镜中的纹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