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字画私人老板收购名人字画私人收购
-
面议
对于被学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书都会有错,我也会犯错,你们可以去做研究来证明我的错误,为什么只是不许我发表意见?”徐小虎一直期待着有人能抨击她书中写错的地方或是有年轻教授拿着这本书去继续考究中国其他古画的创作年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没人与我讨论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我反而好像瞬间由机构与学术刊物间消失,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在《被遗忘的真迹》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这样写道。
在和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实都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却“不喜欢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重新检验每一幅古迹,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无稽之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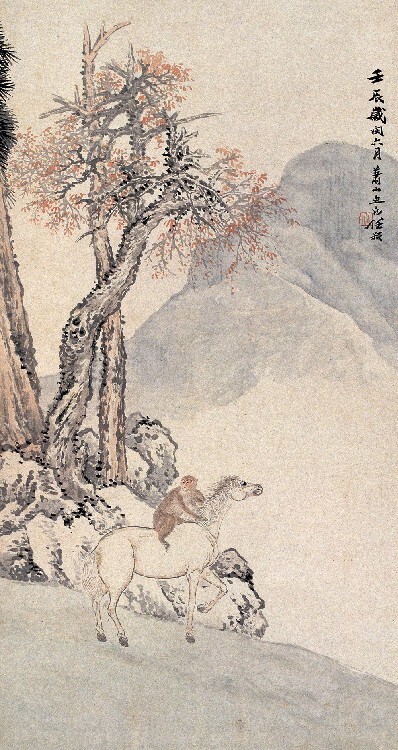
这样的文化通才,前有大师无数,后恐来者寥寥了。
说起傅熹年,同学王世仁和王其明印象深刻的都是“家学渊源”。
王世仁是傅熹年住上下铺的兄弟,大学时曾去过傅家。那时傅家已经从“藏园”搬到西城区大觉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曾任北洋教育总长,自号“藏园老人”,家中藏书万千。王世仁记得,连门道里都堆满了书,书房里满墙都是书柜,放着“二十四史”等古籍。他印象深的是希特勒的水彩画集子,全中国就这一本。
傅熹年的父亲傅忠谟是玉石鉴赏家,1951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当时文物局刚成立,不少人是从外地调来的,住集体宿舍,周末常到傅家聚会聊天。其中,张珩、徐邦达和傅家世交启功等人都是精研古代书画的。他们闲谈间说的都是古书画,有时还展开辩论。有一次说到宋徽宗的柳鸭芦雁图,张珩说柳鸭是真的、芦雁是假的,徐邦达和启功不同意,后来确实在芦雁上发现了问题。
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王其明觉得傅熹年很有钻劲儿。他是红绿色弱,考清华建筑系前就有意识地做“预习”,画画知道自己哪个颜色不准,就注意调整。她觉得,傅熹年被划右派受打击很大,但对他来说也算一个很特殊的成长环境,还收获了知心的爱人。他划右派后,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女友却坚决不改志向,他也毫不动摇,两个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结婚的。
除了画图,傅熹年的文史综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在协助刘敦桢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时,他开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来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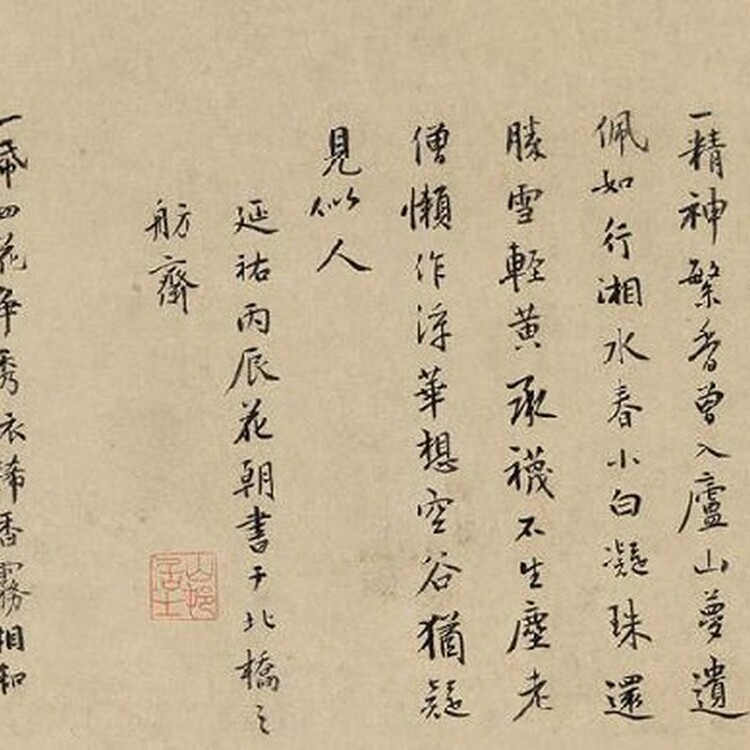
傅熹年还回忆,鉴定组开会时,他和刘久庵常坐在一起,互相交谈。每次提出反对意见,总有人会问:你说不是他画(写)的,那你说是谁画(写)的?可能有感于此,一般鉴定时定其真伪就够了,但刘久庵还进一步研究伪品,尽可能找出作伪者,如指出多件祝允明书法都是吴应卯、文葆光伪作的。刘久庵不但熟悉大名家,还熟悉中小名家,对一些名家的不成功之作,他往往能力排众议定其为真笔。
巡回鉴定工作于1989年底结束,共过目全国6万多件书画作品。作为鉴定成果,出版了10册《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其中编成24卷彩色《中国古代书画图录》
鉴定工作结束后,傅熹年偶然翻阅旧笔记,起了对《百尺梧桐轩图》加以考订之心。因为这幅绘画之精雅、题诗诸人的声名之煊赫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一幅伪作却会有七位同时代名家为它题跋?
通过研究题诗的内容和题诗的时间地点,他判定,画上的梧桐轩主人应是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当时张士诚以富庶的平江(苏州)为中心割据江浙11年之久,在遍布全国的元末起义烽烟中,这里成了一个文学艺术盛的孤岛。傅熹年认为,画的作者应是当时居留在平江的一位名家,其画风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张士诚兵败身亡后,收藏者不得不裁去原款,伪托赵孟頫所作,实是为了将画作保存下来而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因此,此图虽非出自赵孟頫,也有特殊的历史和艺术价值。